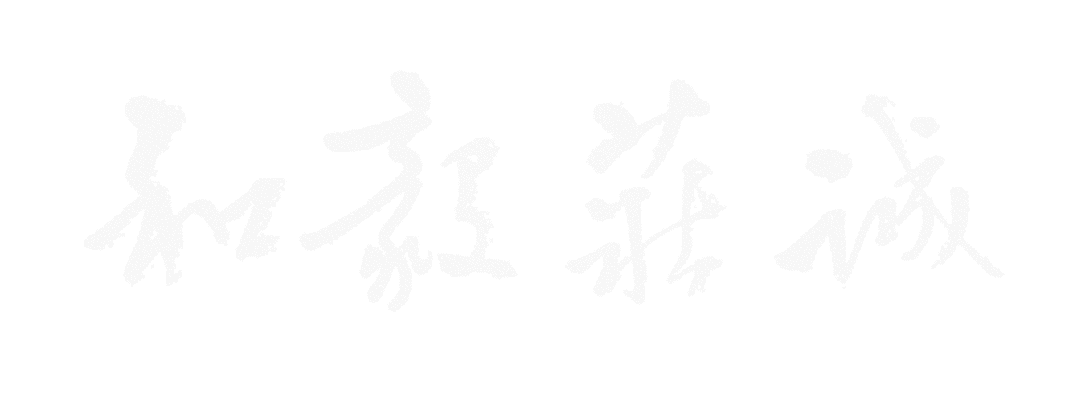
在上海乃至中国的艺术发展史上,钱世锦(上音1960级校友)是一位罕见的“多面手”——他既是精通小提琴的演奏者,也是原创芭蕾的剧本创作者,更是将西方音乐剧引入中国的 “拓荒者”。从上海音乐学院的琴房到上海大剧院的舞台,他的职业生涯跨越半个多世纪,每一次转型都踩在时代艺术发展的关键节点上。这种“跨界”并非偶然的选择,而是源于他对艺术本质的深刻理解:真正的艺术从无边界,无论是芭蕾的肢体叙事,还是音乐剧的歌舞融合,核心都是 “用优质内容连接观众”。而这份视野与魄力的起点,正是上海音乐学院赋予他的专业根基与开放思维。
琴缘初结:从分期付款的小提琴到上音的音乐启蒙
钱世锦与音乐的缘分,始于初中时的一次 “羡慕”。初一那年,班里一位同学师从聂耳的小提琴老师王人艺学琴,每当同学带着小提琴出现在校园,那优美的旋律便让年少的钱世锦心生向往。“我回家跟爸妈说想学小提琴,他们说太贵了,让我学口琴。” 可这份对音乐的渴望并未熄灭,拗不过他的坚持,父母最终在复兴公园旁的琴行,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下了一把20多块钱的小提琴 —— 在那个月薪仅三四十块的年代,这笔开销无疑是家庭的重担。
最初,同学偶尔指点他拉琴,后来经人介绍,他结识了上海音乐学院的朱英老师。朱英是与俞丽拿同辈的音乐家,曾参与著名的女子重奏组,既会拉小提琴也擅长手风琴。为了上课,钱世锦每周要从家里辗转到漕河泾的上海音乐学院校区,“那时候路远,但一点都不觉得累,满心都是想学好琴”。这段求学经历,让他早早感受到专业音乐教育的严谨,也为日后与上音的深厚联结埋下伏笔。
1960年,上海舞蹈学校正式成立,为筹备未来的芭蕾舞团伴奏乐队,上海音乐学院特别开设 “管弦班”。凭借扎实的小提琴基础,钱世锦顺利考入,师从司徒家族的司徒海城 —— 司徒家族的四重奏在解放前的上海颇具名气,司徒海城更是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(上海交响乐团前身)的首批中国乐手。在司徒海城的指导下,钱世锦的小提琴技艺突飞猛进,而学校对 “乐队合作” 的重视,更让他跳出 “独奏家思维”,理解了合奏的默契与平衡。
上音 “管弦班” 的设立,本身就是一次前瞻性的艺术布局:在重独奏、轻合奏的传统音乐教育体系中,学校敏锐捕捉到芭蕾舞团需专业乐队的需求,这种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培养思路,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钱世锦后来的艺术管理理念。
在上海音乐学院的五年里,除了主科小提琴,基本乐科、钢琴、俄文、文化课都未曾落下,而最让他受益终身的,是谭冰若老师的西洋音乐史课。“谭老师从圣歌讲到现代音乐,从瓦格纳讲到理查・施特劳斯,我做笔记最认真的就是这门课。” 钱世锦至今记得,谭老师会专门讲解歌剧的历史与结构,哪怕当时中国鲜少上演西洋经典歌剧,“那些理论基础,后来成了我研究芭蕾、歌剧、音乐剧的‘家底’”。彼时的他未曾想到,这些课堂上的知识,会在数十年后成为他引进音乐剧的 “钥匙”。
芭蕾结缘:从乐队伴奏到戏剧化芭蕾的探索者

《白毛女》剧照
1965 年,钱世锦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,恰逢上海舞蹈学校 “白毛女剧组” 筹备大型芭蕾舞剧,他与同学们组成的乐队直接迁入剧组,成为《白毛女》的首批伴奏乐手。“每天都在排练,还要自己抄谱,陈燮阳当时刚从指挥系毕业,和樊承武一起担任指挥。” 这段每天与芭蕾为伴的日子,让他从 “听芭蕾” 变成 “懂芭蕾”—— 他发现芭蕾虽无台词,却能通过肢体与音乐传递细腻的情感,而《白毛女》“洋为中用” 的创作思路,更让他看到传统与西方艺术融合的可能。
《白毛女》的创作与演出,是中国艺术史上中西融合的早期实践:以西方芭蕾的肢体语言为载体,讲述中国本土的革命故事,这种 “借洋壳装中魂” 的模式,让钱世锦深刻理解到艺术形式可以服务于内容,这一认知成为他后来改编鲁迅作品、引进音乐剧的核心逻辑。改革开放后,国外芭蕾舞团陆续访华,钱世锦的视野被彻底打开。莫斯科大剧院的《斯巴达克》、英国皇家芭蕾舞团的《睡美人》…… 他不仅为这些经典剧目伴奏,更开始研究不同流派芭蕾的特点。当看到斯图加特芭蕾舞团的《奥涅金》时,他深受震撼:“这部剧把戏剧和芭蕾完全融合,没有传统古典芭蕾的固定套式,而是用舞蹈讲完整的故事。”
这份启发让他萌生了创作中国原创芭蕾的想法。他与上海芭蕾舞团的同事蔡国英(第一代 “喜儿” 扮演者)、朱国梁,以及老同学金复载(上音戏剧组的老搭档)一起,尝试将鲁迅作品改编成芭蕾舞剧。他们避开传统的线性叙事,用意识流手法创作《魂》(改编自《祝福》):从祥林嫂被赶出鲁家大门开始,通过独舞、双人舞、三人舞,展现她对“灵魂”及“地狱”的追问,甚至在舞台上用“铡刀”意象隐喻命运的残酷。“当时奚其明作曲,我们反复讨论怎么用舞蹈表现‘阴间重逢’,怎么让观众看懂没有台词的故事。”
《魂》的创作,是钱世锦艺术跨界能力的首次显现:他跳出乐手的单一身份,以编剧的视角重构文学经典,既保留鲁迅作品的深刻内核,又尊重芭蕾 “以肢体叙事” 的艺术规律,这种跨领域整合的能力,为他日后转型艺术管理埋下重要伏笔。此后,他又陆续创作《阿 Q》《玫瑰》《青春之歌》等芭蕾剧本,其中《阿 Q》邀请金复载作曲,以四幕结构展现阿 Q 的命运,舞台上巨大的“Q”字成为经典符号。“写芭蕾剧本不能像写话剧,‘我是你爸爸’这句话,在芭蕾里要靠舞蹈和音乐比划半天,所以必须从音乐角度设计情节。” 这种以音乐为核心的叙事思维,为他日后转型音乐剧引进埋下重要伏笔。
音乐剧启蒙:从百老汇的震撼到 “一定要引进中国” 的决心
《卡门》宣传图
1988 年,钱世锦以 “国际访问者” 身份赴美考察乐队与剧院管理。在纽约,他走访了大都会歌剧院、卡内基音乐厅,看了多明戈指挥的《卡门》,而同学的一句话让他转向了另一种艺术形式:“到纽约不看音乐剧,等于没到过纽约。”
他最初想观看《悲惨世界》,却被告知门票半年前已售罄。直到抵达洛杉矶,在陪同的帮助下,他才拿到两张三楼倒数第二排的票 ——“舞台上的人很小,但两个多小时我全程目不转睛。” 当看到大革命失败后,马吕斯站在空无一人的酒馆里,唱着回忆战友的歌曲,后台的战友们隐隐走出时,钱世锦热泪盈眶:“我从没想过舞台艺术能有这样的节奏,每三分钟就有情节切换,歌舞、布景都在讲故事,太震撼了。”
这次观看体验,不仅是钱世锦与音乐剧的 “初遇”,更是他对 “艺术大众化” 的重新认知:相较于歌剧的高雅疏离,音乐剧以快节奏、强叙事、高互动的特点,更易贴近普通观众,这种让艺术走进大众的属性,与他内心传播优质艺术的初心高度契合。那一刻,他在心里埋下一个念头:“一定要把音乐剧引进中国。”可当时的中国,既无专业的音乐剧剧场,也无市场化的演出机制,“连‘音乐剧’这个概念,很多人都没听过”。钱世锦没有急着行动,而是默默观察:他看百老汇的运营模式,了解音乐剧 “工业化生产” 的特点 —— 道具按波音 747 货舱尺寸设计、服装针脚有严格标准、演出流程如同 “流水线”,“这些细节,后来都成了谈判时的‘功课’”。
他的不急于行动,恰恰体现了成熟艺术管理者的审慎:没有盲目跟风,而是深入研究音乐剧的产业逻辑,这种 “先懂行、再做事” 的态度,让他后来的引进工作少走了许多弯路。
大剧院岁月:五年谈判,让《悲惨世界》登陆中国

《悲惨世界》剧照
1996 年,上海大剧院动工兴建,钱世锦被调往负责开幕后的节目策划。他的办公室设在工地的工棚里,“外面下大雨,里面下小雨,只有一根能打国际长途的电话线和一个 BP 机”。即便条件简陋,他做的第一件事,就是翻出 1994 年音乐剧制作人麦金托什访沪时留下的名片,让助手给麦金托什公司发传真:“希望将《悲惨世界》作为上海大剧院引进的第一部音乐剧。”
麦金托什公司起初并不看好——他们派来的香港代表在考察工地后,才勉强同意启动谈判;1997 年,钱世锦赴悉尼亚太总部谈判时,对方经理甚至不愿让他进办公室,站在门口质疑:“《悲惨世界》是英文母语国家才能看懂的,你们能懂吗?” 钱世锦平静回应:“我们可以打字幕,改革开放这么多年,中国观众能理解好故事。”
这段被质疑的经历,折射出当时中外艺术交流的不对等:国外对中国市场的认知停留在 “文化差异大、消费能力弱”,而钱世锦的回应,既展现了对中国观众的信心,也暗含对“艺术无国界”的坚持。真正的难题接踵而至:对方要求用波音 747 货机运输道具布景,“所有设备按 747 货舱设计,24 小时内从甲地运到乙地,36 小时后装台”。钱世锦算了一笔账:海运虽便宜,但海上漂三周,剧团的食宿开销比空运还高;而国内当时没有波音 747 货机,他们四处联络,在各部门的全力支持下,最终通过公开招标,找到能提供 “门对门” 服务的运输公司,解决了 25 万美金的空运难题。
付款方式的谈判更显艰难。麦金托什公司坚持“签约付 50%,剧团到沪付 50%”,即未开演就要付清全款,“他们说这是国际惯例”。钱世锦据理力争:“中国有外汇管制,必须等文化部报批后才能申请外汇额度。” 经过无数轮沟通,双方最终达成协议:签约后付 30%,剧团到沪付 30%,演出过半付 30%,演出结束付清余款 —— 这个 “中国方案”,后来成为国内引进音乐剧的通用框架。
“中国方案”的诞生,不仅是谈判技巧的胜利,更是中国艺术市场 “话语权觉醒” 的标志:钱世锦团队没有一味迎合“国际惯例”,而是结合中国政策与市场实际争取权益,这种 “既尊重规则、又坚守底线” 的态度,为后续中外艺术合作树立了典范。从 1997 年到 2001 年,谈判持续了五年,期间钱世锦和团队多次赴纽约、伦敦,还专门找到在百老汇演《西贡小姐》的王洛勇请教:“他告诉我们音乐剧的服装针脚要‘三角加三角’,才能让肩膀挺括;还说谈判要讲实力,让对方看到中国市场的潜力。”2001 年 9 月 11 日,在伦敦麦金托什总部,双方终于签约 —— 当天中午的庆祝宴上,纽约“9・11 事件” 突发,钱世锦和团队盯着电视屏幕,既担忧又坚定:“不管怎样,这部剧一定要让中国观众看到。”
2002 年 6 月 22 日,《悲惨世界》在上海大剧院首演,原班主演康姆・威尔金森(冉・阿让扮演者)专程从加拿大赶来,麦金托什公司免费提供全套先进音响。首演结束后,全场观众起立欢呼 15 分钟,21 场演出场场爆满,连台阶上都加了座位。“有人从外地坐火车来,看完又赶回去。” 钱世锦说,那一刻,所有的谈判艰辛都烟消云散——他知道,中国的音乐剧市场,从这一天正式开启了。
《悲惨世界》的成功,绝非偶然的文化事件,它验证了钱世锦与其团队“优质艺术有市场” 的判断,也让中国观众首次直观感受到音乐剧的魅力,更重要的是,它为中国艺术市场注入了市场化运作的基因 —— 从票务销售到宣传推广,从舞台技术到观众服务,每一个环节都成为后来者的教科书案例。
薪火相传:从引进者到音乐剧普及的 “点灯人”
《猫》剧照
《悲惨世界》的成功,让更多经典音乐剧接踵而至:《猫》《剧院魅影》《狮子王》《妈妈咪呀》…… 钱世锦在上海大剧院的 20 多年里,始终坚持 “普及与引进并重”—— 他与他的团队组织团体走进学校、企业,讲解“如何看懂音乐剧”;为《悲惨世界》打字幕时,特意找来上海音乐学院的费元洪(陶辛学生),要求“字幕既要贴合唱词,又要符合中文韵律”;甚至在大剧院建了全国首个音乐剧专用洗衣房,“国外剧团要求服装每天清洗,我们就买工业洗衣机,保证演出品质”。
这些看似琐碎的细节,恰恰体现了钱世锦与其团队极致的专业精神。他们明白,音乐剧的工业化不仅是舞台呈现的工业化,更是后台管理、细节服务的工业化,只有每一个环节都做到极致,才能让观众感受到原汁原味的艺术体验。在钱世锦看来,音乐剧不是高雅艺术的对立面,而是接地气的普罗艺术:“歌剧是农业社会的产物,节奏慢;音乐剧是工业社会的产物,节奏快,贴近现代人的生活。” 他始终强调,音乐剧的核心是“讲故事”,“韦伯跟我聊的时候,连说三个‘story’—— 歌和舞都是为故事服务的,没有好故事,再好听的歌也没用。”
如今已年过八旬,钱世锦仍未离开艺术领域:他为上海音乐学院艺术管理系讲“危机管理”,用《剧院魅影》演出中断的案例教学生应对突发状况;他撰写《世界经典芭蕾舞剧欣赏》《芭蕾音乐剧经典选》,把多年的研究成果分享给大众;看到上海文化广场成为专业音乐剧剧场,看到年轻观众能熟练合唱《悲惨世界》的法语唱段,他倍感欣慰:“艺术的传承,就是看到后来人比我们做得更好。”
钱世锦的“不退场”,本质上是“艺术传承”的责任感使然。他没有止步于引进者的成就,而是通过教学、写作等方式,将自己的经验转化为行业财富,这种传帮带的精神,让中国音乐剧的发展有了更深厚的人才根基。回望从上海音乐学院走出的数十年,钱世锦说自己始终记得谭冰若老师的话:“热爱是最好的老师。” 从分期付款买小提琴的少年,到引进音乐剧的 “拓荒者”,他的每一步都围绕“热爱”展开——这份热爱,既是对音乐的执着,更是对“让优质艺术滋养更多人”的坚守。而上海音乐学院赋予他的,不仅是专业的音乐素养,更是开放包容的艺术视野,让他能在中西艺术的碰撞中,为中国观众打开一扇通往音乐剧世界的大门。
钱世锦的跨界人生,早已超越个人职业生涯的范畴,成为中国艺术市场从 “封闭” 到 “开放”、从 “计划” 到 “市场” 的缩影:他用自己的经历证明,真正的艺术从业者,既能深耕专业、打磨技艺,也能跳出舒适区、拥抱变化;既能尊重传统、传承经典,也能突破边界、开拓创新。而这份精神,正是每一个艺术从业者都应传承的初心与勇气。
文字:杨珺涵(海上音讯社)
图片:钱世锦、上音校友会
指导老师:王翩
责编:程昕蕾
审核:于清
联系我们:
地址:上海市徐汇区汾阳路20号
邮箱:xiaoyouhui@shcmusic.edu.cn
电话:021-53307041
